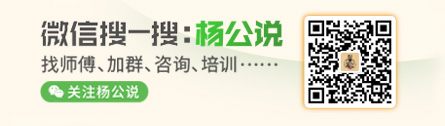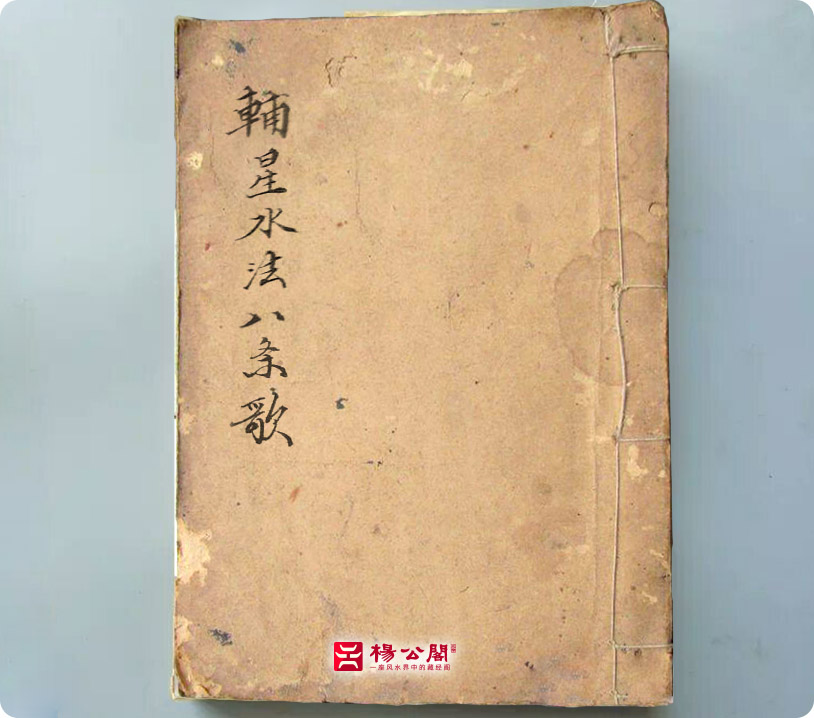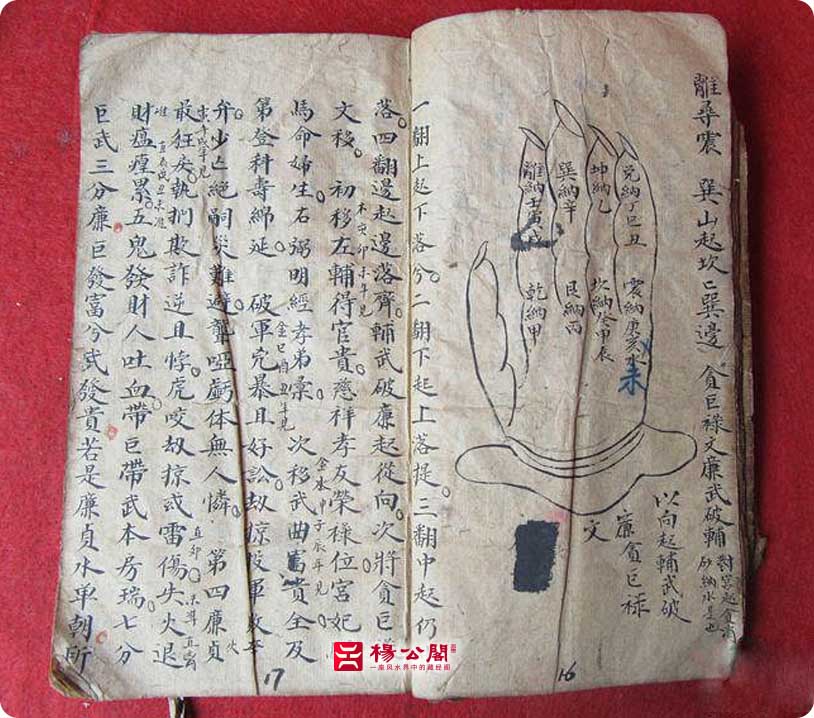药口,收藏杨救贫灵魂的水口
如果说水府贮藏着寒信村人一个久远而不曾更醒的大梦,那么,溯梅江水过寒信峡便是鼎鼎大名的药口坝。
药口坝是个古名,又叫跃口。杨救贫之前这里还有另一个名字:芒滕坝,包含现车溪乡河边、宽田乡杨公坝、段屋乡寒信嶂一带。药口之盛名,缘于杨救贫。杨救贫是百姓对他的尊称,其本名叫杨益,号杨筠松,祖籍窦州(今广东信宜县),唐僖宗时宫廷国师,官金紫光禄大夫,掌管录台地理事。唐末黄巢起义,天下大乱,杨从宫内携了一批风水秘籍从长安逃至赣南,并在赣南带徒授艺,开江西“形势派“风水。杨救贫一生大多活动在虔州、虔化(今宁都县)、赣县(杨仙岭)、于都(寒信峡、梅窖三僚)一带。
关于杨救贫的传说甚多,如十八滩、杨仙岭的来历,虔州城“六街“、二十四井的布局,卢光稠下毒药、杨救贫死于药口等等。在寒信流传最多的是杨救贫移山成峡、临死前在寒信授物与徒及药口毒发身亡的故事。
传说,杨救贫初到这里时,见这里水面宽敞如洋,是个可建府城的风水宝地,便用赶山鞭把旗形山和将军山(因山上有永灵山庵堂,又名庵背山)驱动,欲使之合拢,堵塞水流,令梅江改道,不想时值拂晓时分,一早起妇女见山在移动,惊呼起来,山蓦然而止,遂成了两山夹峙之状,这便是寒山峡了。这个传说,与赣州十八滩、赣县三溪寨九坳传说如出一辙,既表征了赣南文化的同宗性,也显示文化的简单复印其背后所蕴藉的一种特别的恋乡情结。
另一则传说。杨救贫为卢光稠卜得“风水宝地“后,卢担心杨为别人再卜佳地,遂于一日宴请杨,杨虽然对卢有所防范,但终究没有看透卢在阴阳酒壶中做的手脚步,眼见得卢从中筛出酒来饮了,便放心饮了卢预先置于其中的慢性毒酒。宴毕,卢匆匆离城,携身边徒弟曾文灿(另一位于都籍徒弟刘江东)溯贡水、梅江,沿江边山道惶惶奔逃,欲往宁都金精山居住的另一弟子廖禹处去。不想,走到寒信峡,毒性发作,肚疼难忍,便在河岸边稍远处一石头边屙屎,见便呈黑色,杨心知命不久矣,略作思考,遂将三样贴身宝贝--地理书、赶山鞭、神碗放在一侧。与弟子溯着梅江河复向前行了数里路后,杨停下脚步对徒弟说:我的毒性发作了,你回头去看看我屙的屎是黑色还是黄色的,若是黑色的我的命就没了,若是黄色的师傅的命就还有救。徒弟往回了走了一段路便折了回来,佯作高兴地对杨说:师傅,师傅,你屙的屎是黄的,师傅有救了。杨问道:你没有见到我屙屎的旁边放的那几样宝贝?徒弟根本没去,自然没见着杨救贫故意留下的宝贝。杨长叹一声:无缘矣!徒弟重新再返,寻师傅屙屎处留下的三件宝,只遇三个小孩,问可见三样东西?小孩们说,我们捡了一支鞭,一挥动就地动山摇,捡了一只碗,一舀水河都干了,吓死人了,是妖物,我们赶快丢到河里去了。徒弟急问:还有一本书呢?小孩答:书上没写字,我们也丢往河里去了。徒弟急忙往下游寻去,见江面上漂着些书页,就近捞回了一部分。可叹,杨救贫一世奇才,遗世文字极为有限。
传说,徒弟返程追上师傅时,杨已走到了寒信峡前梅江的另一水口,此处江水陡转,暗流湍急,河面狭窄,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开阔的沙坝,形势险要。杨救贫立于岸畔,忍着痛苦,问徒弟:此为何处?徒弟告之:药口。杨苦叹:完了,药已到口,我命休矣!遂对徒弟交代后事:我死后,用石棺石枕葬在这药口坝。徒弟一生与师傅顶牛,师傅说东他偏往西,师傅说白他视为黑,凡事与师傅对着干。杨本是想让徒弟铁棺或木棺下葬的,他算定下葬之处日后必成为河道,他便可以待铁木腐败而再生。岂料,一生不听话的徒弟这回却认认真真照师傅的话去做了,结果,一世英明的杨救贫,先失算于卢光稠后,再失算于徒弟,以致石锁沉江,终身不得再生。
渡我们过河的船夫肖师傅,也是从寒信村繁衍出来的后代。他指着沙滩前一座长满松竹的矮山说,这就是药口坝。他告诉我们:每年都有来自韩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的各式各样的人来这里凭吊杨救贫,记忆中光我渡江送过来的客人就有四五千人,上个月有二三十个香港客人,一上山便个个掏出罗盘,四处奔跑测量,很是神奇。
杨救贫究竟死后葬在哪个具体位置?有人说在湍急的河流中间,有人说挂在悬崖边最终被冲没了……众说纷纭。烈日下,江风浩荡,山野肃穆,悬崖边曾立于明万历年间(赣州知府叶梦熊立)和清代两块纪念碑石,如今作为重要文物安静地保存在于都县博物馆内,现在旧址处的是一堵没有落款的碑石。碑石高大,不古朴,碑文却镌刻得饱满而遒劲,仿佛在虔诚地叙述着一千年来客家人对杨救贫的深深崇拜。在碑石旁,有刚进行过祭祀的痕迹,但见残香几支,烛泪数滴,与着“哗哗“作响的松涛、江风,无言地传达着走近药口坝的人心底的一份情感。
在寒信村人的心中眼里,寒信峡药口收葬了杨救贫的灵魂,故而是神奇而充满魅力的。他们与我们这些搞客家文化研究的人在一点上的了解是一致的--杨救贫死亡之地的记载是“寒信峡药口“。他们补充着,在寒信村,与杨救贫之死的传说一脉相承,寒信滩至今也还存在有屙屎石、棺材石等自然景观。
只是我们驻足的药口坝属于车溪乡辖内,梅江对面又有杨公坝且属于宽田乡辖内,而历史上药口只属于寒信峡,当时并没有段屋、车溪、宽田之说。我以为,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应当尊重当时史实,一千年的时间,往事如风,风云变幻,有多少时事变迁!追溯历史,今天兴国的三僚村,从远古至解放前都属于于都辖内呢,因此,我们又何必太计较今天的三僚被宣传成了杨救贫的重要活动地,成了“中国风水第一村“?既然历史上的三僚属于于都,那么,今天的三僚村因历史因素而成就的人文成果,也就绝不会简单地被理解为与于都无关。
风景中的古村
寒信村的文化远不止于“韩信峡”、“水府庙会”、“药口坝”等诸多的神奇传说,寒信村的文化底蕴是相当深厚而丰富多彩的。而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寒信村,“红绿古三色“文化资源竟然占尽风光!
从寒山峡顺江而行,不过百米,一行巨榕逶迤江边,将绿色风景如长镜头一般拉向梅水尽头。老人告诉我们,过去这里是榕树的故乡,数不清的榕树把村子全然掩蔽,如今,只剩下29株古榕了。古榕多为高龄,仅凭它巨大的身形,百余丈的华盖,一身斑驳的老态,再比较赣州七里镇及贡水、赣江一带的榕树,便可知寒信村需要七八个大人才能合抱的古榕至少有近千年以上的历史。沿河一线的七株巨榕,枝叶相接,竟将河边村径全然掩蔽,自成幽境,行走其间,江水泛绿,榕树流碧,心在摇曳,让人觉得仿佛是在诗意中徜徉。其中还有一对夫妻樟夹生在榕树群中,这是赣南绝无仅有的共生树,但见裸露而发达的根系彼此生长于对方体内,形成完全一体的块茎,两根树干直耸云天,彼此相依,相亲相爱又独立生长的态势,让人感叹之余,想起舒婷的诗歌《致橡树》。
寒信村最大的古榕下,是育英小学。风景秀丽的山川,令育英小学也成了风景中一物。育英小学建于1927年,一直是一所相当出名的学校,除于都本县之外,兴国、瑞金等县的学子也多有来此求学的。建校八十多年来,共培养高小毕业生7500多人,许多杰出的肖氏后人就是从这里走出寒信村、于都,走向世界的。可惜,风雨侵凌,校舍渐危,前些年,通过历届校友们帮助,育英小学旧貌换新颜。值得记录一笔的是,原育英小学的大门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它临梅水而立,风流依旧。
梅水,从宁都朗际的梅岭发源,当穿过一大片杨梅林时,溶了梅的爱恋与诗歌,一路吟咏到了于都寒信潭。寒信峡当真有大将军风范,它以一隘雄威,将梅水的激情尽然敛收,积成深潭,全没了寒信峡上游的湍急感。梅水在寒信潭稍作回漩后,遂以一种平稳、轻盈的姿态复向前行。此后,水面陡然开阔,水也温温柔柔,竟有了些媚态。
三十年前,这里的水面成汪洋状,浩浩荡荡,几不见边,最宽处约近千米,村人告诉我们,当年有一游水高手,在一个水面最阔的汛时,豪情万丈,欲横渡梅江,竟总也划不到对岸,最后生生地累死于大河中央。如今,梅江水瘦了许多,稍会水性的人便可游到另侧,寒信村梅水的浩瀚感成了老人的记忆。大面积的沙滩裸露出来,更是让人惊悸岁月的流变。然而,碧水,沙滩,古榕……却无意中营造出了另一种旖旎风光--寒信峡下游的沙滩宛如一弯人造海滩、天然泳场!便是我们这些仁水爱山之人,也恨不能击水其中,体悟寒信山水之秀美,感受乡村生活之曼妙。难怪寒信出身的肖紫雷、肖紫云兄弟离开了家园,故乡情深,故土难以释放对故乡的恋爱,他们觉得应该作些努力,把寒信营造成山水自然、客家风情融为一体的风景地,并把这片风景地向全社会推介出去!
在村头两棵绿阴参天的古榕下,横亘着寒信村人商业繁荣的见证物--十三级半古码头(村头古榕下还有一座瓦檐也是十三片半的社官庙,寒信人在外地偶遇往往以是否知晓这两个十三个半来验证同乡)。因为前些年修堤,码头的一半已被水浸掩。历史本就是沉浸于岁月之河的。随着河风吹拂,梅江水轻轻拍岸,释放出来的涛声千年不改;一位农妇在古码头浣衣,婆娑的榕树下,竟是入画的极好素材。
码头文化从来是奠定一个地域商业、人口繁荣的重要因素,大凡有古码头存在的地方,历史上必定有过一段辉煌的商业繁荣。从古码头上岸,寒信村沿河一带形成了上街、中街、下街,店铺、旅馆林立,至今仍可见一路的卵石和断垣,街衢痕迹历历可见。可以见证寒信村商业繁荣的还有接官亭。接官亭本是官府的场面之物,但在寒信村却赫然残存着一座风雨沧桑中摇摇欲坠的接官亭。接官亭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为村里显富,专为迎接县乡官员来村里圩上开展公务而建,据说每当官府来人,村官或乡绅们便提前在码头至接官亭一段的道路上铺陈棉被,再覆草席,鸣锣、下跪,接官入厅。接官亭院内曾有一棵三五百年生命的桂花树,为接来的官绅们送去寒信村的热情与芬芳。可惜,前年,这棵桂花树被某房后人以两万元价格卖给了广东人。如今寒信村老人一说起这件事便黯然伤心,觉得毁了祖宗的一样宝。
正对古码头,是寒信村人的精神领地--水府庙,六百年来香火始终袅娜,飘逸中不知散淡了多少肖氏族人和来往船人的祈祷与祝福。水府庙庇护了肖氏族人和来往船人,也庇护了许多忠善之人--1932年,朱德曾率部队在寒信村休整过,朱德还亲自在河坝上给村民做过报告;苏区时期这里还办过学校,“穷人不打穷人“、“红四十师……“等红军标语至今还清晰可见;1939年,抗战期间,八十一军后方医院从赣州搬迁至寒信村驻扎一年有余,还留下伤兵墓地;随后不久,赣州劳作师范迁移到寒信村办学,也历时年余。年年冷暖更迭的四季风,让寒信村人自己都淡忘了许多往事,然而,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却着实让第一次走近寒信村的人感到历史的沉甸甸。
毗邻水府庙,则是肖氏族人的荣耀之物--寿六公祖祠。寿六公祠,聚风聚水,气势轩昂,承接着梅江水氤氲不散的清气,也承接着水府庙长久的喧嚷。在许多客家地,田野里、古道旁,经常可见孤独地散落着一幢或几幢祠堂,如于都杨公坝旁的管氏宗祠、赣县赣江旁的夏府宗祠、全南乌桕坝一隅的李氏宗祠……它们都曾经辉煌,并且里面贮满了故事,但因为离开了聚落,与聚落居民的整个乡土生活系统失了有机联系,失去了它在系统内的特定地位,已不再是血缘村落宗族结构的物化表现,而显得既无生气,也无内聚力。而寒信村的肖寿六宗祠则全然不同,数百年来,这里一直是肖氏族人聚会的主要活动地,也是他们祭祀祖先、弘扬传统的精神领地。
在祠堂内,1958年赣南师范毕业的寒信村联谊会长肖卿豪,满腹经纶,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寒信村的祠堂、庙宇联为一体,借庙宇文化传播了姓氏文化,而村落里形成的祠堂毗邻成群,则体现了四房子孙后代的宗族团结。他告诉我们,自己本来对宗族事务毫无兴趣,退休后,受到村里人爱戴与推崇,感受到家乡人对故园的热爱,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热心于家族事务来了,他这次回村就是受托主持肖氏族谱新修事宜。说到族谱,肖卿豪十分兴奋地说道:寒信肖氏族谱举世无双,至今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自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的五、六、七、八修谱原件,尤其是八修谱不同一般!我们大为不解,他便与8旬老人肖翰桧搬出解放前八修族谱给我们看,才知道缘故--当时县、省及以上的各级官员均为他们修谱题词或作序,如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白崇禧等,其中序即为白崇禧所作。之后,广东、湖南、福建、江西四省均以此谱为准,集2万余肖姓人家99族联修新谱,成为轰动一时之事。
寒信村尚有16幢大大水小的祠堂,如星罗棋布散落榕树下,风格迥异,保存得也相当完整。寿六公生有四子,四房子孙繁衍如斯,枝繁叶茂。到了清康熙年十九年,肖氏后人感恩祖上荫德,遂筑了寿六公祖祠及四房各自的分祠,之后几百年,又有些富绅、官员追随祖辈光荣足迹,又建了数座祠堂或巨宅。
走近这些古祠堂,最让人感慨的是其中一块块镶嵌在古门楼上的匾嶂上题词,诸如“驯鹤素柬“、“瑞映北垣“、“天开文运“等,无不对当时与后代起着巨大的鼓励。传说,寿六公的四房子孙各有特色,并形成“长房富子多,二房点子多,三房才子多,四房舟子多“的口头文化。肖氏族人列举了两个事例,一是清光绪年间寒信村一年出了13个举子,二是2002年高考的赣南高考状元肖忠良即出自寒信村三房肖玉恭之后,据说肖忠良考取了北京大学,并在入学复试中名列第一,肖氏族人津津乐道至今。
寒信村最近的名人是肖忠良,寒信村最古的物却是肖寿六之妻谢氏的墓。肖寿六本人死后,葬回祖地赣县茅店信江营去了,他的四子中有才气的老三肖玉恭也随之葬于信江营祖地。其妻谢氏和她的另三个儿子则被子孙留葬在寒信村做了风水。其实,谢氏墓只能说是坟,因为它简陋得只有一堆荒土和丛丛杂草掩蔽着的碑。村里人叫此地为铜锣坪,肖氏主母的坟踞于铜锣中央的凸起处,是个风水极佳处。据肖氏族人说,历朝历代都想将主母坟修得精致些,请来风水先生,用罗盘测过,竟没有一个人说可以动土,原因是铜锣坪破坏了便没响,肖家的风水便破了。于是,六百年下来,主母坟年年承受着后人的烧香跪拜,却始终外表质朴,日渐荒芜。而后人也纷纷把坟往这铜锣坪做,年代一久,四周层层叠叠的坟地垒成了山,竟高于这铜锣的凸起处,显然,当初的形势早已改变。不过,肖氏族人对老主母的敬重丝毫也不减,在我们走进寒信村时,85岁的退休老师、村民理事会负责人肖翰桧,领我们看过接官亭后,最先把我们领去看的就是这肖氏主母坟……
去过寒信村,感慨良多。赣南古村如散珠碎玉,随处可见。然而,岁月的侵蚀,战争的破坏,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人为的损毁,以致今天还能见到相对完整的古村落已是少而又少了,勉强可以算数的,比如赣县白鹭村、宁都东龙村、寻乌周田村、瑞金密溪村……所以,深山藏玉,寒信村虽然不及流坑、培田,但寒信村以庙宇、祠堂文化,数百年风雨如磐地坚守客家精神与传统,数万人年复一年地坚持开展庙会活动,仅就这一点就决定了它的客家文化传承力量之雄浑,也因此奠定了它的客家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之重要。